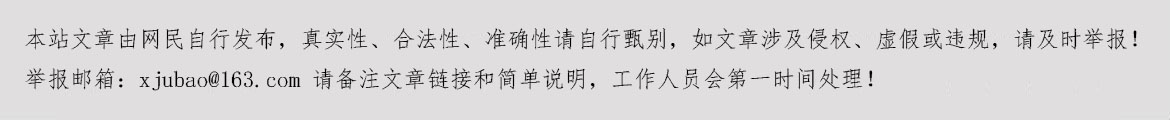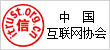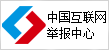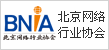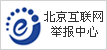鼎铭网是领先的新闻资讯平台,汇集美食文化、体育健康、教育科研、热点新闻、投资理财、国际资讯、等多方面权威信息
巫鸿:北京的钟鼓楼
2021-03-17 19:00:00
中国修建史学家习惯于从平面结构来研究传统北京城。其结果是,相干讨论大多疏忽了北京城的一个紧张特性:在明清的五个半世纪(1368-1911年)中,钟鼓楼是北京城中轴线上最高的两座修建,比紫禁城中的正殿太和殿还要高10来米。但钟鼓楼和紫禁城中宫殿的真正差别还不在它们的高度,而在其是否能被大众瞥见:太和殿深藏于紫禁城的重重围墙之中,而钟鼓楼则袒露在大众视野里。事实上,在明清北京的全部皇家修建中,唯有这两座塔楼可以称为“大众纪念碑”(publicmonuments)。直至现代,它们仍然高耸于周边的商铺和民宅之上,也仍然带给人一种强烈的修建巨障的印象。
清代北京紧张修建高度示意图
20世纪初期的北京钟鼓楼
北京的钟鼓楼是许多笔墨作品所描写的对象,这些作品包括官方文献、纪念性题刻、政府档案、游记、回忆录以及民间传说,等等。检读这些作品,我们发明私人回忆录和民间故事甚少谈及这两座修建的雄伟外观,而每每栩栩如生地转达出写作者对其声响——塔楼上的25面鼓和一方巨钟的敲击声——的高度敏感性。[1]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官方文献和题刻少少提到这些声音,而大多存眷于两座塔楼作为宇宙和政治象征的寄义。[2]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会有如许的分歧?这个分歧又意味着什么?最简朴可能也最可信的答案是:官方文献是由修建塔楼以控制大众报时的人所誊写,而回忆录与民间传说则多为在一样平常生活中直接受钟鼓声影响的人所撰。前者的陈述通常将修建钟鼓楼的意图(intention)与其外观相连,尔后者则通常显示出对钟鼓楼报时声音的接受(reception)。这两类作品相异的内容和存眷点表明了钟鼓楼寄义的两个反差的方面。
好比说,我所能找到的最为流行的描述鼓声节奏的笔墨是北京当地的一句民谚:“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3]另一个著名的北京民间传说也是从非同寻常的钟声得到的灵感。[4]这个故事讲的是明永乐天子敕令铸一口新钟,但铸匠试铸多次也未能使之满足。天子龙颜震怒,威胁要处罚铸匠。铸匠的女儿听说后,为了救父一命,跳入正在浇注金属溶液的铸模中,永远地化作大钟的一部门。父亲虽然在末了一刻尽力捉住女儿,但只救出了她的一只鞋子。这次铸成的大钟十分完满,但在北京住民的耳里,每次撞钟时钟声总听起来像“鞋”的声音,恰似铸匠的女儿总在寻索着她丢掉的那只鞋。
我对钟鼓楼的讨论从这些影象和传提及始,而不是从天子的布告或朝廷公文出发,是由于这些非官方的文献生存了钟鼓楼消散了的一个方面,亦是它们在相干研究中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如今这两座修建只管外观完好,却已经完全寂静。在一个现代观者的眼里,它们的意义似乎全然寓于形制和装饰当中。换句话说,当听觉不复存在,视觉就成为其汗青价值的最主要和明显的证据。简直,艺术史家或修建史家似乎可以满足于对钟鼓楼的修建特性举行观察和分析,或依据其屡次修缮的相干文献重修其汗青。但这种满足的伤害性在于我们现实上将自己置于钟鼓楼修建人及设计者的态度上——我们对修建设计及其预设象征性的夸大过于密切地呼应了这些人的态度。而在这种夸大中所缺失的是:钟鼓楼到底如何真正发挥作用?尤其是从其台阁传出的声音引发了怎样的经验与想象?
如今无声无息、死气沉沉的钟鼓楼提示我们注意到这个缺失。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促使我提出一个双重的要领论来讨论钟鼓楼。第一,我们不能仅仅依赖钟鼓楼的物质实体及文献档案来理解其汗青上的“纪念碑性”,而必须实验着“凝听”并苏醒钟鼓楼消散的声音,并由此想象这些声音所动员的社会交流和空间转换。第二,苏醒这些声音的唯一要领是激活“汗青上的听众”的影象——那些在私人回忆录和民间传说中生存的平凡北京人的影象。现实上,“找回消散的声音”可能是对“影象”最好的比喻了。但北京钟鼓楼传出的不是一般的声音,而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纪念碑性”的、在数百年间支配了千百万民众一样平常生活的声响。
*
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元多数首建的鼓楼已被多次重修和修缮[5],现存鼓楼的形制和所在大抵生存了明初永乐天子于1421年迁都时敕建的风貌:楼高46.7米,占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是一座相当壮观的木构修建。绿瓦顶的重檐下饰以彩色装饰带,其余部门全部涂以朱漆。由厚砖墙加固的塔楼底层现实上形成整座修建的高台基座,将木构的楼体举起离地30米高。在鼓楼顶层向四方远望,老北京城一览无余。顶层的大通间里原来安置有25面鼓,每面以牛皮绷面,其中的一面大鼓直径1.5米。如今唯有这面鼓得以幸存,朝廷官员原来用以测定伐鼓时候的铜刻漏和其他计时器都已遗失。
20世纪初期的北京鼓楼
北京的钟楼位于鼓楼北面,二者相距很近。这座钟楼的汗青也可追溯到明初——元世祖时期的钟楼位置略微偏东,如今已无迹可寻。现存的钟楼不像鼓楼那样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木构修建,而是早在1745年就已改建为砖石结构——原来的木结构钟楼毁于大火,清乾隆天子遂做出了这个决定。乾隆还在钟楼前直立了一方大石碑,上面所刻的铭刻记载了他希望通过重修钟楼到达“亿万斯年,扬我人风”的目的。乾隆天子对艺术鉴赏涉猎颇深,因而新建钟楼的设计也很可能含有美学和象征的意义:这座修建外观凝重典雅,与繁华华丽的鼓楼既形成鲜明对照又相辅相成。鼓楼庞大而雄伟,钟楼则纤瘦而雅致。钟楼通高47.9米,甚至比鼓楼还要高,是修建者刻意寻求屹立效果的有力佐证。鼓楼象征着雄性之阳,钟楼则代表了雌性之阴。与鼓楼一样,钟楼也是两层修建,底层为其高基。一口高5.5米、重6.3吨的巨钟悬挂于顶层开放式穹窿内室的中心。室四面不设门,钟声的传扬因而没有丝毫拦阻。就鼓楼而言,虽然顶层四周设有门窗,但定点伐鼓的时候总是流派大开,使鼓声得以传至都城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