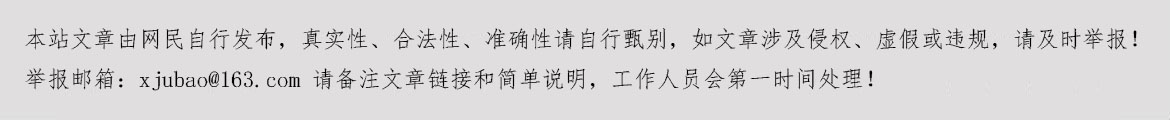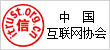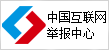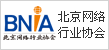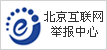鼎铭网是领先的新闻资讯平台,汇集美食文化、体育健康、教育科研、热点新闻、投资理财、国际资讯、等多方面权威信息
合肥母亲携子女坠亡背后:为什么施暴者“消失”了?
2021-03-25 10:31:00
一桩家暴悲剧发生时,施害者通常不愿意承认家暴,一方的失声甚至“神隐”,让关注点几乎全倾斜于另一方——受害者身上。
3月12日早晨,合肥一名29岁的女性携一对儿女从24楼跳下,三人不幸身亡。据家属透露,死者生前曾遭受过丈夫的家暴,事发前几日申请离婚,处在离婚冷静期。
死者的妹妹发文表示,为什么人没了,很想一问究竟,但目前男方及其亲属都联系不上。
而在家暴伤害中,一方“消失”的场景似曾相识,如前段时间的“拉姆案”。在一篇十万加的文章中,拉姆这一名字出现的次数是86次,她的前夫的名字是37次,并且是以“唐某”出现的。
很多人都知道受害人叫拉姆,却鲜有人知道向拉姆泼洒汽油的凶手叫唐路。
回顾以往舆论关注的家暴事件会发现,过度聚焦受害者可能会带来对其过往举动的非议和质疑,这无疑会给受害者带来二次伤害。
相比之下,原本最应被追究、被审视的对象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正如美国律师兼教授古德马克所说:“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却忽略了那些造成问题的人。”
拳头代替沟通
有一些施暴者在做出伤害另一半的举动后,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某社交平台上的反家暴讨论区里,不仅有受害者求助的帖子,也出现了施暴者的求助信息。
一个动手打了妻子的男性发文称,害怕自己变成一个长期施暴的人。他想改变自己,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以及一个心理健康的父亲。
另一个男性表示,他在一次醉酒后因与女友产生口角而打了她几巴掌。事后他觉得懊悔,并寻求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在自述中,他坦承小时候目睹的一次父亲殴打母亲事件,对自己造成的影响。
白丝带终止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负责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张智慧向大白新闻表示,他们经过观察研究认为,大部分施暴者的暴力行为都是习得的,而不是天生的。
“男性的家庭暴力行为可以从原生家庭、社会上以及学校里习得。因为暴力对他来说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并且,我们的文化系统、社会、家庭容许、甚至鼓励他这么做。主流文化鼓励男性阳刚勇敢,鼓励其用身体力量说话,鼓励他用暴力行为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境下,暴力使男性觉得自己更具有支配力,更像个男人。即使他实施了家庭暴力,多数情况下不会受到太大的惩罚,甚至有时根本不会有任何惩罚。”张智慧说。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召集人、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方刚认为,家暴是性别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下的产物,本质上是权力与控制。
接受“白丝带”辅导与干预的顾伟曾谈到了自己第一次实施暴力行为的场景。
当时,顾伟与妻子正并排看电视。妻子想让他把收入交给自己理财,但顾伟一听到自己的钱要由女人保管,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重重地踢了妻子一脚,踢在了她的小腿上。
顾伟说,自己一开始是提高音量让对方感到恐惧,随后是否认、贬损对方,如果到这还没有控制住对方,接下来就是轻微的暴力行为,而最终,将演变成全面、更加严重、频繁的殴打行为。
他剖析了自己曾经的家暴行为:“其实就是施暴者的控制欲望在作祟。在外面受了委屈、掌控不了局面,回家之后就想掌控一些权力,想在小家庭当中实施一下。”
顾伟称,自己的成长环境充斥着暴力。他的爷爷是村子里出名的家暴者,不仅会打顾伟的奶奶,也会打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顾伟的姑姑。他的父亲虽然没有打过母亲,但行走在外时,也常通过争吵、武力来解决问题。
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顾伟在17岁时出现了暴力行为。他打了自己的母亲,父亲对此没有表示,而他的舅舅则是代替他的母亲,还给了顾伟重重的一巴掌。以暴制暴。
在这个家庭中,暴力代替沟通在人与人之间循环着、代际传播着。
最终,拳头落在了力量最小、最弱势的群体——女人和孩子身上。
家暴行为治得好吗?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陈敏在《涉家庭暴力案件审理》一书中将家庭暴力的施暴人分为三种类型:
一、偶犯型施暴人。这种类型偶尔施暴,后果一般不严重。这一类型如果愿意接受认知和行为矫治,预后效果不错。但是,如果任其发展为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这一类型则可能从偶犯型逐渐转变为两副面孔的施暴人。
二、两副面孔型施暴人。施暴人中的大多数,善于伪装。在社会上温和、平静,能为别人着想;在家庭中要求遵循男尊女卑的传统,以暴力行为使受害人服从。这一类型明知故犯、逃避责任,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主动求治。因此,他们接受认知和行为矫治的同时,必须有违法便受惩罚的压力,否则效果并不好。
三、疯狗型施暴人。这一群体不乏反社会人格和精神病患者。反社会人格的暴力行为严重,可能因虐待家人情节恶劣、伤害家人致残或致死被判刑,也可能被妻子以暴制暴杀死。而因患精神疾病而对他人施暴的人,占比非常小。
陈敏总结道,这三种类型的人数在社会上呈正态分布,即第一、第三种类型的人少,第二种类型的人多。
张智慧则发现,向“白丝带”求助的男性施暴者中几乎没有疯狗型施暴人,大多数都是第一种类型——正与伴侣处于恋爱关系或者婚姻早期,而且暴力行为并不是非常严重。如果这些人接受专业、及时的辅导和干预,暴力行为将会明显减少甚至消失。
“白丝带”曾在2019年9月开展了一次“家庭暴力施暴者矫正辅导试点项目”,起初共有8位施暴者参与活动,后来有人退出,也有新人加入。
他们每周六聚集在北京,进行长达6、7个小时的讨论:结合自己的相关经历,一起讨论、反思“支配性男性气质”;认识家暴的本质、规律及伤害;学习处理情绪和沟通。
2020年2月,这一累计超过80个小时的活动结束的一个月后,“白丝带”公益组织向施暴者的伴侣发放了《小组成员伴侣反馈表》和《小组成员暴力变化频次表(伴侣反馈)》,用以检测项目的效果。
结果显示,除了小组中的暴力行为比较严重的那位成员外,其他人的暴力行为出现了明显的减少,个别人的暴力行为消失。
这个结果令人感到惊喜,但项目负责人方刚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这一项目只对轻微型施暴者有效,而应对施暴程度严重的类型,效果并不明显。
张智慧坦言,目前在中国,除了法律手段,还未有专业的组织或者方法来应对较为严重的施暴者,如疯狗型施暴人。
据“橙雨伞”公益组织介绍,“RSVP”((Resolve To Stop The Violence)即“决心制止暴力”,成立于1997年,是美国第一个针对有暴力犯罪史的男性监狱改造项目。
项目成员需要严格参与每天8小时、每周5天的活动,他们围坐在一起,思考和梳理自己的错误行为给自身、家庭和社区所造成的伤害,并学习如何处理和修复伤害。其中,还有一项颇为重要:倾听家暴受害者的讲述。
吉米·埃斯皮诺萨在接受RSVP学习之前,有长期虐待女性的历史,而他现在是RSVP项目的一名推动者。他向记者描述了第一次听到女性受害者亲述时的感受。(图文说明来自“橙雨伞”)
据“橙雨伞”消息,2005年的数据显示,与旧金山国家监狱整体平均水平相比,16周的RSVP学习使暴力犯罪者出狱后一年内的再犯率降低了82%。
相对于发展较为成熟的RSVP等项目,国内针对暴力犯罪者的专业矫治仍是一片空白。
当他们加入反家暴进程
“白丝带”负责人表示,自2010年开通求助热线以来,每年大约会接到四五百人的来电,其中只有二三十人是施暴的男性。
“而这二三十人当中,持续打电话的人很少,能够出现在线下活动中的就更少了。一方面。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错了;另一方面,男性不愿意求助,觉得求助的话等于承认自己是弱者。他们没有下决心改变,动力不足。社会机制里没有鼓励他去改变。他们也不敢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但实际上有的人还是能改变的。”张智慧告诉大白新闻。
大白新闻留意到,在施暴男子的求助帖里,也有人会因憎恨施暴者而留下一些激烈的言论,如“狗改不了吃屎”“你去死吧”。
其中也不乏客观的声音:“施暴者也是暴力的受害者,他们也需要我们的理解和帮助,所以请大家理性,不要有泄愤的心理”“只有受害者参与,我们是永远无法终止家庭暴力的。只有施暴者也积极地参与,我们才有希望能真正终结家庭暴力。”
不过,也有一些担忧的声音:如果帮助实施暴力的人,会不会给受害者造成一种对方会改变的印象,因而阻碍其离开的步伐。
对此,张智慧多次强调,施害者一定要有强烈的自救、改变的意识,暴力行为才有望得到纠正。否则,女性一定要果断选择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不要寄希望于对方会自己改变。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召集人方刚也表示:“家暴中的实施暴力的人如果自己没有改变的强烈愿望,没有经过系统专业的干预,是具有循环性的。”
顾伟是白丝带辅助的案例中最成功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敢以实名和真面目示人的曾经的施暴者。
很少有施暴者像顾伟一样,最终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有错。
“有一些人觉得不是自己的错,他会淡化、否定自己的错误,他觉得很多人都这么做,或者他可能找一个借口,比如女方也有问题,双方都有冲突,然后他不小心、忍不住。”张智慧说。
张智慧回忆道,顾伟当时很坚定。我们看到他很认真地学习了反家暴的知识,看到他想改变的努力。他认识到如果自己不去改变的话,这辈子就毁了。并且,他不想把暴力传递给儿子,他希望暴力终止在他这一代。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决定以真面目示人,借此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监督。
未来是否还会有更多的“顾伟”站出来,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加入反对家庭暴力的行列,不得而知。
撰文:郭若梅